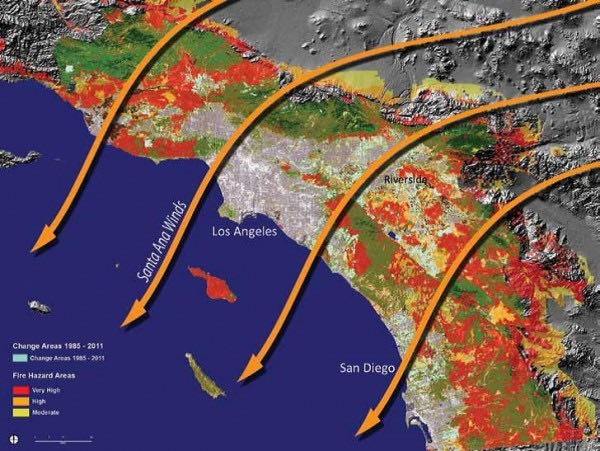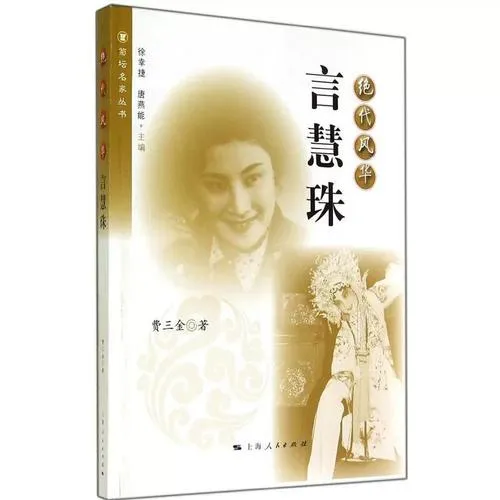(前言:今年六月詩人節,我去加拿大溫哥華參加「開創華文文學時空」的文學論壇,見到了瘂弦與洛夫兩位詩壇大師;又與北二女同學胡有瑞、朱立立 (荊棘) 相聚;更承加拿大華文作家協會徐新漢會長,在百忙之中,開車陪我們三位老同學去美麗的 VanDusen 植物園賞花觀木…..)
VanDusen 植物園位於溫哥華市的37街與Oak街交界處,原是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局的高爾夫球場,後由富商VanDusen (Whitford Julian),卑詩省 (British Columbia) 省政府,與溫哥華市政府各出資一百萬元,將球場改建為植物園,於 1975 年對外開放,並以 VanDusen 命名。
植物園佔地 55 acres(英畝),有花木250,000株。花園設計極為精美,連路邊的一株小草,池邊的一塊石頭都美得動人。遊人信步走去,時而蓮塘,時而瀑布,時而松柏成林、綠野仙蹤,時而草長鶯飛、雜花生樹。朱立立和我,跟著照相機,隨興而行,一路鮮花鋪地,蝴蝶飛過,人在園中彷彿來到了人間天堂、伊甸樂園。
Dogwood (山茱萸,直譯為「狗木」)
山坡上的小路兩邊,杜鵑花 (Rhododendron,映山紅) 剛開過,而山茱萸正開得滿山遍野,密密麻麻,層層相疊,紅得耀眼。
我曾住紐約上州,家中後園有一株山茱萸,每到春天,一片粉紅花色從落地窗映入屋中,美得叫人屏息。然而這次我在園中所見的山茱萸,似乎特別的紅艷濃密,與我記憶中的清淡高雅很不相同。後來我從她的名字「Kousa Dogwood」才發現,這花樹竟是 Chinese Dogwood (中國山茱萸),在中國叫「四照花」,那是因為她的美艷「光彩四照」而得名。

除了四照花,植物園中的山茱萸多種多樣,讓我大開眼界,嘆為觀止。其中 Pacific Dogwood 不能不知,她是溫哥華所在地,卑詩省的省花。
Sino Himalayan Garden (中國喜馬拉雅區花園)
「中國喜馬拉雅區花園」是非常難得一見的花園,園中種植各種喜馬拉雅山區的花卉與樹木。我們去時,Himalayan Poppy (綠絨蒿) 正在盛開,有藍白兩色,色彩淡雅清麗,是一種極為珍貴的高山花卉。

六月底是溫哥華的 poppy花季,「罌粟科」家族中的花朵,色彩繽紛,迎風招展,其中包括橙黃色的加州州花 California Poppies (加利福利亞罌粟,又叫花菱草)。
Peony (牡丹花)
中國的「國色天香」,牡丹花,雖遠涉重洋,從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長安古城,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溫哥華,但她依然風姿不改,華麗富貴,艷冠群芳。
在英文中,Peony 既是牡丹 (Tree Peonies),也是芍藥 (Bulb Peonies)。但在中國,牡丹與芍藥是不同的:牡丹是花中之王 (木本),芍藥是花中之相 (草木)。我這次在園中所見的「peony」似乎都是芍藥,但在我看來,不論是木本或草本,她們都一樣的雍容華貴、艷光照人。
Voodoo Lily (直譯為「巫毒百合」)

植物園中最奇特的花木,當推巫毒百合。這花有她獨一無二的容貌,叫人一見難忘。她來自地中海地區,據說會散發臭氣來引誘蒼蠅,但時間很短,只有一天,所以並不惹人嫌厭。我在網上還看到我們愛吃的「蒟蒻」(魔芋)居然跟她有點親戚關係,奇怪吧!
Cherry Blossoms (櫻花季)
園中還有24種不同的櫻花共一百株,我去也晚,錯過了花季,雖然沒有親眼目睹花開時的盛況,但也可以想像百株櫻花齊放時的那種華麗之美。